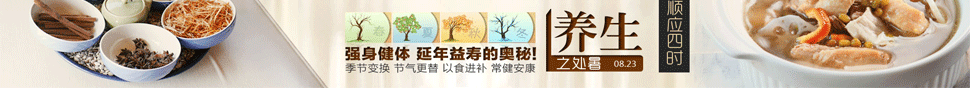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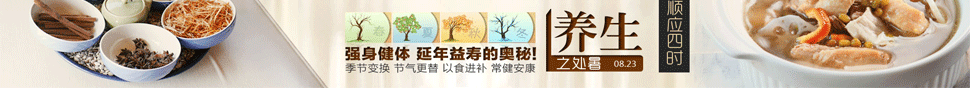
黄仕沛教授查房实录2
病例1
主管医生:患者男性,50岁,因“言语不利,右侧肢体乏力6天”入院。缘患者6天前晚上4点钟去厕所时,出现右侧肢体无力,但尚可行走。至次日早上8点,医院就诊,考虑为“脑梗死”,予对症治疗后,于当日12点转入我科。入院时测右上肢肌力0级,右下肢肌力Ⅲ级,反应减慢,感觉性失语。经补液、扩容和中药治疗后,目前情况:患者精神倦怠,言语涩謇,偏瘫,口舌歪斜,头晕,口气重,喉痰鸣,腹胀,大便秘结,舌质暗,苔黄腻,脉弦滑。
中医诊断:中风-中经络(痰热瘀阻)
西医诊断:脑梗死
主管医生:你好,黄教授来给你看病了。
黄教授:好点没有?
主管医生:他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黄教授:嗯,应该好多了吧。嘴唇还是暗红的。有没有发热啊?
主管医生:没有,肺部感染的情况和痰不是很多。
黄教授:精神还是不太好。总是想睡觉吗?
患者家属:没生病的时候很精神,这几天好像要把这些年没睡够的觉都补上去一样,老是打哈欠,一直想睡觉。
黄教授:大便通了没有?
主管医生:昨天通了。
黄教授:腿能抬起来吗?
患者家属:前几天不行,这两天稍微好一点。
黄教授:手呢?能动一点吗?患者家属:基本上不行。
黄教授:口干吗?有没有口苦?
主管医生:他可能不太理解您的问题。
黄教授:看一下舌头。(指导患者伸舌)舌质比较红,苔黄厚腻。脉有点弦。
病例2
主管医生:患者赵某,女,26岁。因“视物模糊1年,加重伴嗜睡,反应迟钝1周”于年9月20日收入院。缘患者于年5月第一次起病,出现复视,视物模糊,考虑为“视神经脊髓炎”,经激素冲击治疗后遗留视物模糊。后于年10月出现左侧肢体麻木,经激素冲击治疗后麻木消失,但仍有视物模糊。入院前1周,患者出现精神差,嗜睡,反应迟钝等症,遂往我院就诊,门诊拟“视神经脊髓炎?”收入院。现症见:患者精神疲倦,面色萎黄,嗜睡,视物模糊,反应迟钝,言语混乱,记忆力严重下降,站立行走受限,无发热恶寒,无异常汗出,无胸闷心悸,无腹痛腹泻,纳差,二便正常。查体:神志清楚,高级神经功能减退,双软颚上抬乏力,咽颚反射迟钝。四肢肌力Ⅳ+级,四肢肌张力正常,未见肌肉萎缩及肌束颤动。生理反射存在,病理反射(-)。舌红苔黄腻。辅助检查:年10月我院头颅及颈椎MRI示:①脑干多发性硬化。②颈椎MRI平扫未见异常。体感及视觉诱发电位示:考虑视神经脱髓鞘改变。
主管医生:黄教授来给你看病了。
黄教授:自己感觉怎么样?
患者:还行,就是有点累。
黄教授: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经常讲错话?
患者:有时候知道。黄教授:但是你控制不住?
患者:有时候讲得太快了。
黄教授:讲得太快就会乱,是吧?没有幻觉?幻听?
患者:没有。黄教授:有时候记忆不太好,是吧?
患者:是。
黄教授:记不记得月经什么时候来啊?
患者:说不清楚。
黄教授:那昨天晚上吃饭记得吗?
患者:记得。
黄教授:晚上睡觉怎么样?
主管医生:睡得比较多。
黄教授:你白天一直打瞌睡,那晚上睡得好不好?
患者:睡得好。
黄教授:晚上没有醒来过吗?
患者:有啊。
黄教授:晚上睡得好的话,为什么又会醒呢?
患者:因为吊着针。
主管医生:她有时候说话是答非所问的。我们经常问她同一个问题,但结果却不一样的。
黄教授:看看舌头。口干不干?
患者:有点。
黄教授:喝水多不多?
患者:蛮多的。
患者家属:昨天一天都没喝水。
黄教授:但是她自己说喝水是蛮多的。大便怎么样?
患者:还行。
黄教授:手脚都没问题?行动方不方便?
主管医生:走路还可以,手脚的神经系统检查都没有什么异常。
黄教授:有没有头痛?
患者:有一点点。
黄教授:有没有头晕?
患者:没有,就是有一点点头痛,好像平时没有休息好一样。
黄教授:摸摸脉。脉还是有点滑,左脉沉一点,右脉是弦滑。
病例3
主管医生:患者黎某,女,40岁,因“右眼睑下垂伴四肢乏力3年,加重半年”入院。缘患者于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睑下垂,视物重影,当时未予重视,年11月3日出现言语不利,说话带鼻音,吞咽障碍,饮水呛咳,晨轻暮重,遂在我院住院治疗,诊断为“重症肌无力”,出院后一直口服溴吡斯的明片,症状可控制。半年前自觉服药后症状改善欠佳,一直在我院门诊行中西医药调理,症状仍有所加重。此次入院患者于年9月10日行胸腺切除术,术后出现肌无力危象,予行血浆置换术后症状缓解,日前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。现症见:患者精神疲倦,面色?白,白天汗出较多,畏冷,四肢稍乏力,晨轻暮重,无发热,头晕头痛,恶心呕吐,腹胀痞闷,四肢抽搐等症,纳、眠差,小便调,大便稍软,月经量少色暗,内含少许血块。舌淡苔白,脉沉。
主管医生:您好,我们请黄教授来给你看病了。
黄教授:她的眼睑下垂没有了?
主管医生:现在下垂得不是很明显,这次住院主要是觉得全身乏力。
黄教授:想睡觉吗?
患者:没有啊。
黄教授:白天还是很精神的?
患者:是。
黄教授:很多汗出啊?
患者:我怕冷,所以有时候不敢把被子拿开,就有点汗。
黄教授:以前声音也是这样吗?
患者:不是,之前插了管。
主管医生:可能和重症肌无力的症状没完全好也有关。
黄教授:看看舌头。舌质比较淡,口淡不淡?
患者:不淡。
黄教授:想不想喝水?
患者:想喝水。
黄教授:喜欢喝热的还是冷的?
患者:热的。
黄教授:大便怎么样?
患者:现在正常,每天都有。
黄教授:好,我们回去讨论一下病情吧。
黄教授:今天看到三个病人,都挺有意思的,好像初步印象都可以跟经方对得上。从西医角度,我就不分析了,大家都比较清楚。从中医角度来说,这三个病人有共同点,也有各自特殊的地方。共同点就是都属于中医“中风”范畴。因为中医“中风”并不单单是指现在的脑血管病。其实传统的“中风”包括了“痿证”。原来《千金方》说“中风”有四种,包括偏枯、风痱、风懿和风痹。风痱就是“痿”了。《黄帝内经》无“中风”一病,但有“三厥”:煎厥、大厥、薄厥,是吧?“阳气者,烦劳则张,精绝,辟积于夏,使人煎厥。目盲不可以视,耳闭不可以听,溃溃乎若坏都,汩汩乎不可止。阳气者,大怒则形气绝,而血菀于上,使人薄厥。有伤于筋,纵,其若不容,汗出偏沮,使人偏枯”“血之与气并走于上,则为大厥。厥则暴死,气复反则生,不反则死”。比如说那位视神经脊髓炎的病人“目盲不可以视”,就是视神经的问题,属痿证,跟《黄帝内经》“厥”差不多。所以后世认为“中风”相当于《黄帝内经》的“厥”。其中薄厥就是阳气上迫。薄者,迫也。煎呢?就是煎熬的意思。使人煎厥之后出现什么呢?“目盲不可以视,耳闭不可以听”。就是来得很急,而且看不到又听不到,甚至昏迷。这些都是对“中风”的描述。等到了金元四大家的时代,大家开始怀疑传统治疗方法的效果,于是出现“火、气、痰”的学说:河间主火,东垣主气,丹溪主痰。到了明代,王履提出了“真中”跟“类中”的说法,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“中风”跟张仲景说的“中风”不一样,所以叫“类中风”,只是类似而已。可是到了张景岳的时候,他更认为这些都不是风,因此不要叫“类中风”了,干脆叫“非风”好了,“非风”就不是风了。而清代叶天士开始明确了“内风”的概念,提出肝肾不足,阴虚风动。到明末初的时候,有西医进来了,认为“中风”跟血压高、脑出血有关,以民国的“三张”(张伯龙、张山雷、张锡纯)为代表,其中张山雷写了一本《中风斠①诠》,里面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对“中风”的看法,逐渐把所有肢体的活动障碍都归入在内。张锡纯有建瓴汤、镇肝熄风汤等方子,大家应该很熟悉了。其实,回顾中医“中风”一证的发展沿革,历代名家,各执一词,很多都是从病名上做文章,而不是从治法上下功夫,所以让人难以把握。我觉得仲景的“中风”治法,现代并没有过时。陈修园说:“火气痰,三子备;合而言,小家伎。”就是认为从金元开始的“中风”论述都是“小家伎”,违背了张仲景的诊断和治疗。当然,我们并不是否认后世的发展,只是提醒大家要怎样对待张仲景关于中风的论述和方治。
至于中风的方治,我觉得《金匮要略》的中风篇对后世影响很大,所列方剂,至今仍有其实用价值。可惜现在的中医内科书只介绍了《金匮要略》中风按中经络、中脏腑的分类,而忽略了经方的治疗。《金匮要略》中风篇里面的方,一个是侯氏黑散,一个是风引汤,一个是防己地黄汤,还有就是续命汤和千金三黄汤。侯氏黑散:“治大风,四肢烦重,心中恶寒不足者。”它里面有14味药:菊花、白术、细辛、茯苓、牡蛎、桔梗、防风、人参、白矾、黄芩、当归、干姜、川芎、桂枝等。比较复杂。但我看这个方的关键是一味——菊花。因为方里面其他的药分量很少,比如说桂枝三分,桔梗八分,防风十分等。而唯独菊花四十分,说明这个方以菊花为主。结合后世的经验,大剂量的菊花常常可以平肝熄风。防己地黄汤,这也是一个怪方,我形容是“不可理喻”“治病如狂状,妄行,独语不休,无寒热,其脉浮”。我们的切入点就是认知功能障碍,如狂状,妄行,独语不休,胡话等。跟刚才那位患者是不是很像?这个方组成是5味药:生地黄、防己、防风、桂枝、甘草。它的特点就是重用鲜生地黄,是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所有方中用生地黄最多的方。我认为这里重用生地黄是对神志有作用,包括炙甘草汤、百合地黄汤也是。
另一首就是风引汤。风引汤“除热瘫痫”。它的组成有8味金石药:龙骨、牡蛎、滑石、石膏、寒水石、赤石脂、白石脂、紫石英,还有大黄、干姜、桂枝、甘草。特点是什么呢?重镇潜阳!我想我们药房可能凑不齐整个方。叶天士很喜欢用潜阳药治疗中风。当年叶天士和徐灵胎都很出名,都在苏州开业,但是叶天士比徐灵胎大20岁,是老前辈。他早年看到徐灵胎开的方,认为用药非常杂乱,喜欢用金石药。但是若干年以后,他才发现徐灵胎原来喜欢用金石药是唐以前的方,包括《外台秘要》《千金方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等经方,于是感叹这个徐秀才所学是有渊源的。后来叶天士在学习徐灵胎经验的基础上,自己再去解读。我感觉他是领悟了风引汤等方后,才开始运用大量的金石药。叶氏虽然有不足的地方,但是也有聪明之处。他说中风是肝肾阴亏导致,组方原则是金石药、凉肝药和滋阴药。“肝阳一证,必须介类以潜之,柔静以摄之,味取酸收,或佐咸降,务清其营络之热,则升者伏矣”。这是他的精髓所在。而这个组方原则实际上就是上面那三首方的主药组成,风引汤是金石药,侯氏黑散是清肝药,防己地黄汤是滋阴药。后世很多方都是根据这几个大法组成。不过,法归法,方药归方药。我不相信法,只相信方,就像徐灵胎说:“一药有一药之性情功效。”比如说芍药甘草汤可以治脚挛急,或者腹中急痛,后世的解释是什么呢?芍药酸,甘草甘,酸甘化阴,听起来理论很明白。但是我觉得这样解释要不得,因为倒过来是讲不通的。如果不用芍药和甘草,用其他的酸甘药行吗?显然是不行的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后世的理论来解释张仲景的方,但是不能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选药,更还原不了经方。比如说镇肝熄风汤之类的方药,虽然是根据上面的理论而来,但却替代不了经方。续命汤仍然是续命汤,如果尝试按照相关的理论组织一首方,并不能代替续命汤。又如解表用麻黄汤,桂枝汤。但是后人发展了,用“夏月之麻黄”香薷代替麻黄,是吧?如果在续命汤里面用香薷代替麻黄,行吗?当然不行!所以我觉得经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。那天刘方柏教授讲麻黄汤有八大证:“太阳病,头痛,发热,身疼腰痛,骨节疼痛,恶风,无汗而喘者。”这是任何一首方都不可代替的。方中麻黄解表发汗,平喘,如果按这个思路组织一首方的话,疗效绝对和麻黄汤不一样。另外,麻黄汤八大证里面有头痛,身疼腰痛,骨节疼痛等四个痛证,其他的解表药都不能解决这四个痛证,只有麻黄汤可以。所以说方证很重要,我们一定要抓住方证。麻黄汤有麻黄汤的方证,桂枝汤有桂枝汤的方证,小柴胡汤有小柴胡汤的方证。不能说要解表就把所有的解表药都用上,好像有人用银翘散加桂枝,这是什么意思呢?如果连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,分析病机有什么用呢?所以不管用什么理论,都要辨方证。比如说中风,出现妄行,独语不休,这就是防己地黄汤的方证。然后再分析体质如何,适不适合用?阴虚的程度怎样?没有阴虚见证又怎么办?这样才能掌握此方的用法。我觉得经方最基本的思维就是方证。我们要掌握张仲景是怎么用的,但不要过于强求去了解为什么,因为很多情况下是了解不了的。就像我们买了台电脑或者电视机,只要会用它们就够了,而不用理解为什么会出图像,会有声音,是吧?我们是临床医生,照用就好。当然,如果能够理解病机的话,就最好了,因为方证后面都隐藏有病机。
具体到这几个病人,我觉得大体都可以从这4首方入手。
第1个脑梗死的病人,我认为可以4首方组合:
麻黄15克(先煎),大黄15克(后下),防风15克,生地黄90克,石膏90克(包),桂枝15克,滑石60克(包),龙骨30克(包)。
第2个小姑娘,嗜睡,舌苔白腻,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防己地黄汤:
麻黄15克(先煎),生地黄克,制附子25克,防己15克,细辛10克,防风15克,桂枝15克,甘草15克。
最后一个重症肌无力的病人,可以用续命汤合千金三黄汤加减:
北芪克,川芎9克,麻黄15克(先煎),当归24克,桂枝15克,党参30克,甘草30克,枳实20克,干姜6克。
主管医生:您刚才没有讲到千金三黄汤?
黄教授:千金三黄汤也是中风篇的附方,组成有黄芪、麻黄、黄芩、独活、细辛。其特点是黄芪与麻黄同用,非常适合这个病人。
主管医生:我发现这几个病人的处方里都有麻黄,会不会有副反应呢?
黄教授:我刚刚看了这几个病人的心率都不是很快,麻黄主要的副反应就是让病人心跳加快。所以《伤寒论》里面讲麻黄要先煎,去上沫。同时我用麻黄是逐步加量,最安全的用量一般是12克,但是每个人的耐受能力不同。我通常12克开始,然后慢慢递增到有些反应为止,或退后3克。如果有急性、刻不容缓的病情,那么就要马上用大剂量。另外,麻黄一般要和桂枝同用。为什么麻黄汤有桂枝呢?后世的解释是桂枝助麻黄解表,其实不是这样。麻黄该解表的时候自己就能解表了,不需要桂枝助,用桂枝的目的是减少麻黄的副作用。《伤寒论》第64条说:“发汗过多,其人叉手自冒心,心下悸,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。”为什么发汗过多会心悸?现在吃西药发汗会不会心悸?都不会。所有的发汗药中只有麻黄会造成心悸。所以张仲景说的“发汗过多”,是如实地反映临床,这是用了麻黄以后造成的心下悸,可以用桂枝甘草汤解决。所以《伤寒杂病论》里面大部分情况下,麻黄都和桂枝一起用,比如说续命汤、麻黄汤、大青龙汤、小青龙汤等都是这样。刚才的方子里,因为药房里金石药没有那么多,只能用龙骨、石膏、滑石,都需要包煎。另外,风引汤里面有大黄。大黄是治疗中风非常好的一味药,特别是针对颅内压高的病人,它可以改善颅内压,但是一定要大剂量。所以研究经方一定要重视方证,先从药入手,再理解方,再理解证。
主管医生:黄教授,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给重症肌无力的患者用这么大量的甘草呢?
黄教授:为什么我们用经方的时候,很多病人都觉得好像很热而受不了呢?这时候我们可以重用甘草和大枣,可以中和温性。如果有些病人热证很明显的话,还可以加石膏。另外,我用甘草还考虑到它有类似激素的作用,能够调整免疫功能。其实,干姜也有这样的作用。比如说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,实际上就是口、眼、阴部溃疡,里面用了大量的甘草和干姜。为什么口腔溃疡还用干姜呢?其实张仲景不在乎热不热,里面有大量的甘草垫着,所以我们照用甘草泻心汤的效果很好。我日常用麻、附、辛、姜等辛热药,病人甚小反馈有喉咙痛、流鼻血等不适,关键就是要掌握甘草、大枣的使用。大家看看当归四逆汤用多少大枣?25枚,因为里面有细辛、桂枝、当归等都是辛燥温热的。吴茱萸汤,也是要重用大枣。可惜临床上大家很容易忽视这一点。
主管医生:今天真的是又上了一堂课,非常谢谢黄教授!原来我们都是从中医内科的角度想问题,现在听您讲完以后,感觉回到了正确的辨证上,相信这对我们临床选方用药都会很有裨益。再次谢谢您!
首届国际经方班,黄教授以“《金匮要略·中风》续命汤小议及各方在临床上的运用”为题的讲座广受欢迎,得到一致好评。与讲座不谋而合,此次查房恰为中风患者,可谓理论的回顾,临床的见证,课程的延续。三则病案,一则诊断为“脑梗死”,一则考虑“视神经脊髓炎”,一则诊断为“重症肌无力”。若从西医辨病思路着手,疾病南辕北辙,病因迥然不同,难以归纳共通之处,亦难以想象使用类似方药治疗。黄教授崇《黄帝内经》及仲景之“中风”,认为传统的“中风”应涵盖痿证,故“视物模糊,嗜睡,反应迟钝”当属“中风”,“右眼睑下垂伴四肢乏力”亦属“中风”范畴。侯氏黑散、风引汤、防己地黄汤、续命汤以及千金三黄汤。他人或重此四方的病机治法。黄教授却是更重相应方证,提出经方最基本的思维就是方证,当据仲景所载方证,一一对应,区别适应证和禁忌证,选用合适的方药。第一则病案,典型的“中风”表现,可以四方组合;第二则病案,神志症状明显,故取防己地黄汤,另伴有嗜睡、反应迟钝等阳虚情况,需加麻黄附子细辛汤;第三则病案,从风痱辨治,用续命汤。故虽同为“中风”,治疗却有异。临床识病因,究病机固然重要,但黄教授另辟蹊径而辨方证,亦不失为事半功倍之法!——转录自李赛美主编《理论与临床讲录》(卷三)
注:①斠:[jiào],1.古代量谷物时平斗斛(hú)的用具。2.校正。
-END-有用就扩散
有用就点在看相关阅读:
《黄帝内经》生气通天论篇第三I版权声明
本文摘自
作者/黄仕沛,何莉娜。编辑/刘继芳
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,如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,请随时与我们联系。喜欢黄仕沛前辈的书,欢迎购买正版图书多多支持
I投稿邮箱085803
qq.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