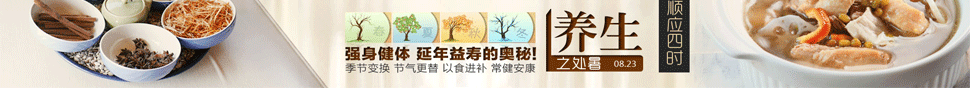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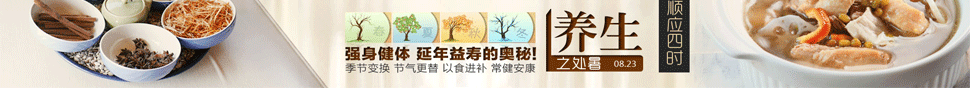
父亲的老物件
孙虎林
父亲离世整整二十五年了,他佝偻的身躯,晚年因意外受伤一瘸一拐的步态,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父亲一生辛劳,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,平凡至极。但父亲却因为一些不无特殊的物件,证明了他的不凡之处。这几样小东西,我都见过,至今保有一些或鲜活或模糊的记忆。几枚银针
小时候,家里有个老式衣柜。柜子上方的土墙上挂了一面玻璃镜子,它承当全家人的梳妆任务。镜子正下方有个长方形红色匣子,匣子里装着一些零碎东西。有一天,我乱翻匣子,突然发现里面有一节指头粗的竹管,竹管一头用棉花堵着。我好奇地抽出棉球,顺手颠倒竹管,几根粗细不等的银针掉了出来。这是什么呀,比母亲常用的缝衣针长多了。它们又细又长,银光闪闪。正当我对着太阳光打量银针时,四姐过来了。她一把夺过银针说道:“这是爸爸的宝贝,赶紧放下。”于是,我看着四姐将几枚银针小心翼翼装进那节竹管,放进匣子。改天,东头五婶苦着脸走进我家院子。刚一进门,她就朝我父亲喊道:“三哥,快给我扎一针,牙疼死了,一宿没睡。”五婶中等身材,黄白脸庞,身子骨不大好,很少出工干活。好在丈夫是小学校长,吃穿用度不愁。五婶进了堂屋,坐在炕边,一手托着腮帮,牙疼得嘶嘶吸气。父亲摸出一根银针,先在淡蓝的煤油灯火焰上烤了烤,而后用药棉将银针揩拭了几下,找准五婶耳根后的穴位,一下扎了进去。父亲一边慢慢捻动银针,一边问五婶疼不,五婶说有点酥麻。父亲让五婶尽量放松,不要想牙疼这件事儿。片刻后,父亲缓缓抽出银针。五婶一脸轻松,感激地笑了。随后,五婶和我娘拉了一阵家常便愉快地回去了。父亲追出门叮咛道,扎针只能缓解疼痛,还得去大队医疗站找医生看看,吃些止疼消炎的药。五婶回说知道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父亲给人扎针治病,一股自豪之情油然而生。只是不明白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哪儿来的银针,他的扎针医术又是谁教的?这一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在我的记忆中,从那以后,村里人谁要是牙疼了,便来我家扎针。多年以后,听四姐说,父医院一位大夫送的。父亲结识那位大夫,是我翠巧姐的养父介绍的。翠巧姐很小的时候送给了人家。养父是位画匠,走村串乡给人画箱柜,也画棺材,三姐出嫁时的箱柜就是翠巧姐她养父画的。鲜红的底漆上,以金粉勾画出花卉鸟兽,再上一层土漆,鲜亮生动,可漂亮啦。但父亲究竟是跟谁学的针刺疗法,终究是个谜。我们姐弟一概不知。父亲在世时,我们没有好好问过他,真后悔。父亲最后一次使用银针,和我四姐有关。有一年春天,已经出阁的四姐一大早跑回娘家。一夜牙疼,疼得她浑身冒汗,脸上火烧火燎。父亲虽然经常给街坊四邻扎针治牙疼,但给自家闺女扎针,却格外小心。人常说,医生不敢给自家人开药治病,父亲虽说不是真正的医生,但也有这种顾虑。他右手捻动一根银针,对我四姐说道;“碎女子,你不怕爸一针下去,把你扎成哑巴?”四姐说:“只要牙不再疼就行。”父亲在和自己的小女儿开玩笑,变着法儿让女儿放松。果然,一针下去,四姐牙疼立马缓解,脸色也舒展了许多。这以后,父亲再未给人扎过针。再后来,这几枚银针便找不见了。一把剃刀
还是在那个红色匣子里,我见过一把剃头刀。老式的,木把,刀背厚厚的,黑黑的,刀刃银白色,闪着寒光,装在一个小盒子里。我偷偷拿出来把玩过,小心翼翼避开锋利的刀刃。心下纳闷,父亲从未用它给人剃过头,刮过胡须,要它干啥。再说,父亲本来就不是剃头匠。邻村有个小个子剃头师傅,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。每隔一段时间,他就挑着剃头挑子来了。挑子一头是小火炉,炉子上坐着铜脸盆。一头是上下两层的抽斗,里面装着理发工具。他的剃头刀很锋利,亮闪闪的,泛着冷光。通常,他先给我父亲剃头,再用手动推子给我理个童花头。我曾经问师傅:“我爸又不给人剃头,要那刀子干啥?”师傅拍拍我的脑袋,朗声答道:“瓜娃,你爸的剃刀是给人治病的。”说毕,哈哈大笑。我听后更糊涂了。多年以后,父亲告诉我,他的剃刀是给人放血治病的。那一刻,我有点愕然,心里怕怕的。见我一脸迷惑,父亲提起了一件往事。那年冬天,隔壁我锁儿爸的媳妇存英半夜发病,肚子疼得在炕上打滚。我四婆喊我父亲赶紧过去看看,他一听就知道是咋回事。从匣子里摸出那把剃刀就跟过去了。进屋一看,存英疼得满头大汗,身子缩成一团,嗓子都喊哑了。我父亲赶紧吩咐我锁儿爸点亮煤油灯,就着灯火把剃头刀烤热,给我锁儿爸使了个眼色。他使劲压着媳妇手脚,我父亲一个箭步上前,在存英的脊椎骨处一刀切下去,她哼了一声,全身软瘫。我父亲一看,不觉倒抽一口冷气。不同别人,存英的伤口涌出一团黑血。坏了,怕没救身了。看着我四婆期待的眼神,我父亲轻轻摇了摇头。果然,天还没亮,存英就走了。看情形,她得的是绞肠痧,一种当时要命的急病。可怜她那年还不满二十岁。后来,我还听二姐说过一件事。那年,她在大营中学上学,有一天碰见一位小脚老太。老太听说了我父亲的名字,喜出望外,一把抓住我二姐,激动地说道:“女子,你爸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前年冬天,我肚子疼得死去活来,多亏你爸用剃头刀在我背上割口子放血,我才活了过来,还好心嘱咐医院处理伤口。女子,你爸的剃头刀救了不少人呀。”二姐听后高兴地笑了。后来,父亲用剃刀还给村西头我大嫂治过病。可惜那时我太小,没能亲眼看看。不过,即使我想看,父亲恐怕也不让看。那场面想想都怕人,这种民间救人的土方似乎有点不登大雅之堂。至于父亲从哪儿学的这门绝技,至今仍是个谜。一节龙骨
依然是在那个红色匣子里,我找到一个包得紧紧的纸团。一层层打开后,发现一段灰白色骨头。于是,我把它拿到院子里,丢来扔去当玩具玩。四姐看见了,赶忙捡起来,告诉我这是龙骨,是爸爸眼里的灵丹妙药。什么,龙骨,恐龙化石?那太珍贵了。我问四姐这真个是恐龙化石吗,四姐想了想,说她也不确定。一天,我玩耍时,不小心被野草划破手,流了不少血。四姐看见后,取出那节龙骨,用刀子刮了些粉末,敷在伤口上。很快,血止住了,也不疼了。原来,龙骨有这么神奇。说来好笑,从此以后,我竟然盼着流血,只是为了见证龙骨神奇的止血作用。长大以后,看了一些药理书。才知晓龙骨有着镇静及缩短凝血时间的功效。实际上,龙骨是一味中药,为古代哺乳类动物象类、犀类、三趾马、牛类、鹿类等的骨骼化石。至于父亲当年何以懂得龙骨的药理知识,也许跟他对中草药感兴趣有关。父亲壮年时有个生意上的朋友,后来,父亲让我拜那位友人做了干爸。那时,父亲和我干爸农闲时就进秦岭山挖药材,一路挖到汉中。将关中的黄芩、柴胡、防风等中药材卖到那里,再将陕南特有的草药运回关中。受父亲影响,我小时候也爱挖药材。我们村在沟边,崖畔坡坎长着不少中草药。我挖过柴胡、黄芩、防风等。最喜欢的是远志。它叶茎细长,开着紫色小花,很好看。村北沟边一道土坡上长着不少远志。不过,这种草药收拾起来比较麻烦,必须把根上的表皮剥离下来晒干,药材收购站要的就是远志根上的干皮。有一次,在县城中街的药材收购门市部,营业员把我的远志根皮放在簸箕里颠来簸去,他们不要粉末。那一刻,我心惊肉跳,在心里祈求他千万手下留情,他要再簸下去,还会剩下几两呢。最终,我的远志换回三块多钱。我即刻冲到新华书店,买下那本早已相中的小说《儒林外史》,花去二元四角。余下的钱,我在东街食堂买了十来个肉包子。那包子小小的,里面包着一块纯瘦肉,可香啦。一节龙骨串起一段往事,激起我的一段草药情怀。只是,那节神奇的龙骨再也找不到了。一副石头眼镜
眼看再有三两天就要过年了,老天不睁眼睛,生生捂下一场大雪。好不容易放晴了,村外一片银装素裹,淡红的阳光照在雪地上,眼睛晃得难受。父亲要上县城跟年集,上次忘了买笊篱。走出家门时,我看见父亲戴上了他的那副石头眼镜。我有些奇怪,石头眼镜不是在夏天才戴吗,冬天雪地有用吗?看我不解,父亲说戴上石头眼镜可以抵挡刺眼的雪光,要不会得雪盲。说罢,父亲鼻梁上架着石头镜,神气活现地进城去了。我在他身后大喊着,“爸爸,不要忘了买挂鞭炮。”父亲当宝贝一样珍惜的这副石头眼镜,实在不怎么好看。在我看来,简直就是一件早已过时的古董。镜片圆圆的,镜架是黄铜做的,咋看咋别扭。父亲却说这副石头镜质量好,镜片上品。旧社会只有财东和账房先生戴得起。父亲告诉我:瓜娃,你不知道,石头镜可不是石头做的,是水晶做的。戴石头镜可以敛神养目,消肿去热。从前,爸眼睛不舒服了,不用看病买药,戴几天石头镜就好了。看我来了兴致,父亲摘下眼镜,教我辨别真假石头镜的方法。父亲将镜片正对太阳,让我仔细观察。他说,真品镜片上,可以看到淡淡的均匀细小的横纹,或者柳絮状的物质,这些就是水晶石的天然纹路。接着,父亲将眼镜在阳光下晃了晃,我从镜片上捕捉到了他说的那些美丽纹路。我确信父亲的石头镜是真品了。事实上,父亲的老哥儿们几乎人人有一副石头镜,来我家打川牌的刘姓老人就常年戴副石头镜。他留着一撮山羊胡子,披着一件羊皮大氅,可神气了。那年月,石头镜几乎成为老年男人的标配。老汉们戴着石头镜,抽着旱烟,蹲在墙根下晒暖暖,要多休闲有多休闲,要多惬意有多惬意。在老人们的眼里,品相好的石头镜不啻为身份的象征。所幸父亲的石头镜保存了下来。可惜镜片上有了明显的裂纹,原装眼镜盒也不见了。依稀记得那镜盒扁扁的,上下抽斗式,材质奇特,好像是鲨鱼皮做的。我看见它时,已经磨损不堪,有些年头了。去年回家时,我把这副石头镜带回到宝鸡了。我要珍藏它,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老物件了。怎么说呢。属于父亲的时代渐行渐远,他曾经把玩过的物件几成文物。在慨叹沧海桑田的巨变之时,我心中惆怅不已。是的,旧时风物大多已成绝响,所幸亲情赓续,绵延不已。那么,就让我们在对祖先的缅怀中感念生活吧,惟愿物换星移中岁月永恒,思念永恒。年5月13日注:图片均来自网络,仅供学习与分享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图文如有侵犯您的权益,请告诉我们,我们会第一时间处理,谢谢。继续阅读
孙虎林:看麦孙虎林:白杨潇潇孙虎林:夜半人语高声时孙虎林:头镰春韭孙虎林:白蒿正当令孙虎林:春在陌头荠菜香孙虎林:把脉春天孙虎林:老宅孙虎林:扫院子孙虎林:挂在大杏树上的红萝卜孙虎林:数星星赵林祥:长篇小说《西安是个坳》(全文)孙虎林,岐山县凤鸣镇人,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中学高级教师,民盟盟员,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多年来笔耕不辍,在各级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一百多篇。作品散见于《宝鸡日报》《陕西工人报》《语文周报》《教师报》《秦岭文学》等报刊。散文《树殇》获第一届“古风杯”全国散文大赛优秀奖。散文《马道巷》入选《宝鸡文学60年·散文卷》。出版有散文集《青春祭》。现任教于宝鸡市某中学。
岐山作家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fangfengcaoa.com/ffcpf/7134.html

